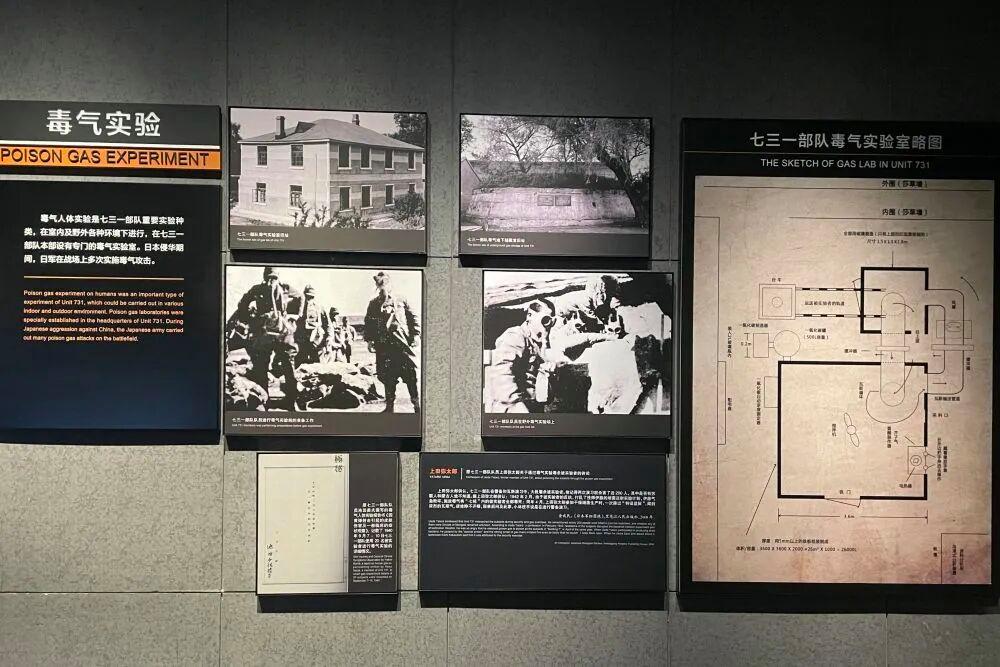摘 要 文章从语言学、社会学、哲学等多种角度,对“腐败”一词的内涵进行了论述,指出“腐败”不仅指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还有社会公众的腐败行为,而后者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使我们的反腐斗争不能彻底进行。因此有必要对公众腐败现象加以重视。
关键词 腐败 公众 政府官员
如果界定腐败,学术界至今仍众说纷纭。许多论者有将腐败狭窄理解的倾向,认为:只有政府官员通过运用或操纵权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获取私人利益,才能称之为腐败。将腐败扩大到公众,会从根本上混淆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界限,容易使反腐败斗争偏离正确方向。对于上述观点,我们不敢苟同。不可否认,腐败主要是以政府官员为主体的,但政府官员的腐败不是腐败的全部,还存在另一种腐败:公众腐败。
公众腐败存在的词源辨析与实证
政治学与社会学意义上的腐败,是从生物学意义中借用或转化来的。其生物学意义是指事物失去原有性质的规定,由良性转化为恶性。向政治学与社会学转义后,并没有规定腐败仅是政府官员所为,而是泛指人们的思想、行为的堕落,组织、机构、系统失去良性机制与功能,是对历史与现实必然合理性的违背。在英文中,腐败的动词与形容词形式为corrupt,意为不道德的、不诚实的、舞弊、受贿、转化的等;其名词形式为corruption,是对腐朽糜烂事物的全景式静态描述。就英文意义而言,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腐败并非为描述政府官员的劣行所专用,因为它还有“行贿”、“非道德”等含义,显然,行贿者并非一定是政府官员,大量情况下,扮演行贿者角色的正是社会公众。
公众腐败现象可以在历史与现实中找到佐证。
众所周知,世界资本主义的萌芽是与亚平宁半岛上的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联在一起的。按历史的可能逻辑,意大利将成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历史的可能并没有在意大利成为现实。自14世纪末到17世纪,意大利发生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J·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指出:当时的意大利充斥着反政府反法律情绪;非道德主义盛行;公众追求放纵、任性、唯我独尊,混乱的男女关系成为时尚;抢劫、行刺、凶杀等恶行频繁不断,预谋犯罪、匪盗成群、打家劫舍司空见惯;很多传教士变成了强盗头子。即使在平静时期,一些人毫无目的地“为犯罪而犯罪”,寻求犯罪快感,流氓、强盗、黑社会势力充斥于整个社会。当城市惩治罪犯时,人们的同情心都在罪犯一边。著名的思想家马基雅弗里为本民族的社会腐败痛心疾首,他认识到:此时的腐败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而是“大众的腐败”,整个社会的腐败,“大众的道德如此彻底败坏,以至于法律也无力约束他们”。
中国目前虽然没达到公众腐败遍地的程度,但公众腐败确实象瘟疫一样蔓延着。
表现之一,公众道德伦理生活呈混乱状态。有些公众对腐败言行的耻辱感与犯罪感丧失了,在过去只能偷偷摸摸地在阴暗角落里干的不光彩行为,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不用避讳他人。在孩子入托、升学、工作调动、评职称、分房时,请客送礼的行贿行为,似乎成为公众较为普遍的模式。更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厚黑术,其中包括送礼术、行贿术、拍马术、投机术等等。
表现之二,行业不正之风或部门的歪风邪气盛行,尽管党和政府为纠正行业不正之风而三令五申,尽管有些品格高尚者不参与。教育界,一些普通教师参与了向学生乱收费的活动;在交通部门,一些普通乘务员以车谋私,敲诈勒索顾客,机场、车站的餐饮业谋取暴利已到了非治不可的程度;在商界,假冒伪劣产品林林总总,从事坑蒙拐骗、投机倒把的并非全是政府官员;文学艺术界,本是塑造人类美好灵魂的高雅殿堂,近几年斯文扫地。社会上大量出现的低劣粗俗作品,正是出自一批痞子文学家之手。
表现之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目前,我国出现了一些为世界一切文明国度里社会舆论所不齿的丑陋现象:卖淫、赌博、贩毒吸毒等,有些属于犯罪,有些则是腐败。还有一些人从事迷信活动、信神信鬼。上述现象在中国发生绝不是个别的,据估计,我国的吸毒者已有数十万,迷信者与赌博者多如牛毛。这些人的社会责任心、上进心正在消解,恢复其昂扬斗志与健全的人格,决非易事。
公众腐败存在的逻辑证明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腐败的实质是以权谋私,核心是钱权交易。政府官员掌握权力,所以,腐败只能来自政府机关的官员。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只看到问题的一方面,而忽视了问题的另一方面。众所周知,任何交易市场都是由交易双方并存而存在的,失去交易的任何一方都不会形成市场。在权钱交易活动中,拥有权力而缺钱的是政府官员,需要以权弥补金钱的缺欠,与政府官员对坐从事交易的并不见得一定是政府官员,大量情况下是缺少权力而拥有金钱的非政府官员。政府官员正是在非政府官员所拥有的金钱的诱惑下,接受贿赂,为贿赂者提供一定的优惠权,使之获得更大的利益。也就是说,在权钱交易市场上,没有买方的卖方是不存在的,同样地,没有卖方的买方也是不存在的,而买权的一方往往是拥有金钱而缺少权力的普通社会公众。
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逻辑过程,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寻租行为”。70年代,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布坎南提出寻租理论,目前我国的一批学者用这一理论分析腐败。用寻租理论分析腐败,虽然并非尽善尽美,但我们可以通过解剖寻租过程,证明公众腐败的存在。这一理论认为,权力寻租就是一种腐败行为,租金指的是追求凭借权力对资源的垄断而造成涨价的那部分差价收入。以政府与企业为例,政府对企业管制,大大增加官员对企业干预的种种权力,这种权力的设置被称为“设租”。为了多得“租金”,企业向官员行贿,从租金中得利的官员力求保持原有的租金制度和设立新的租金制度。由设租到寻租,产生一个贪污腐败果因相联的恶性循环圈。就整个社会而言,某些公众在整个寻租活动中扮演了极不光采的角色,以租金为诱饵,吸引政府官员上钩,拉拢腐蚀政府官员,牵着政府官员的鼻子走。在瓜分“租金”的过程中,某些企业与公众虽然不是绝对的主角,但更不是可有可无的“跑堂者”。
以上我们由权钱交易逻辑的共存性出发,分析交易中拥有“钱”的一方,得出公众腐败存在的逻辑结论。我们还想进一步分析交易中拥有“权”的一方,同样也能得出我们的逻辑结论。
如果权钱交易的“权”,一定是政府的权,则权钱交易中拥有权力者,一定是政府官员,则腐败专由政府官员所为便顺理成章了,这就排除了公众腐败存在的一种可能性。但是,这里的“权”一定是政府的“权”吗?我们认为,权钱交易中的“权”并非绝对来自政府,政府的行政权只是权力的一个特例。权钱交易的“权”有一部分是泛化的权力,而非政府权力。所谓权力泛化指的是由于职业权力的迅速崛起、膨胀和蔓延而出现的权力自行分配现象。权力泛化为公众腐败的存在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职业权力不同于政府权力,不一定是正式授予或委任的,而是自任自居的,它的实施者并不象政府官员那样正式发布命令或否定性裁决来使另一方顺从,而是凭借掌握的各种资源(有形的、无形的)的控制和掌握,迫使希求获得资源者就范。它有时也表现为一种对称关系,即一方在某一领域权利可以为另一方的职业权力拥有者在另一领域所补偿、回报或抵销。因此,谁实际控制或掌握某一种为对方所急需的社会资源,谁就取得了这种权力,而不管他是在政府机关工作,还是平民村夫,都会成为特定资源的占有者。原因在于社会分工造成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职业,能转变为权力的资源也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那些与人民日常生活需要息息相关的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有形商品与无形劳务,谁能利用职业分工之便把持了这类资源,那么他实际上取得了对他人的控制权。人们之所以常常将权力与政府官员联系在一起,而忽略了普通老百姓,原因在于政府权力是一切社会权力的核心,特别是长期以来的集权制,政府力量渗透到社会公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左右支配着人们的命运。但政府行政权力并不能取代其它的社会权力。随着集权走向适度分权,政府权力对公众控制的松动,使得集中在政府少数人手中的行政层级权力结构体系的稳定性受到挑战,社会公众拥有的职业权力将发挥重大作用。由此可知,权力的泛化使权力由政府向社会溢出,其拥有者不再仅限于政府官员。与此相关,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有可能发生在各种社会管理部门和行业的职位承担者身上。一些特权行业可能刮起席卷全行业的不正之风,参与者不仅仅是本行业的官员,很大部分乃是普通职工。
政府官员的腐败就是政府官员的腐败,这似乎是同义反复、不证自明的道理,但细究起来,这仅是一个从非腐败官员角度观察腐败官员的腐败行为得出的结论。若从腐败官员的角度来看,会得出新的结论。在实施腐败行为过程中,政府官员在心目中进行的角色置换而导致官员角色缺位,其腐败已转化为“公众腐败”。有必要说明的是,尽管这种置换仅发生在官员的意识中,但毕竟是一种特定时间与空间的“公众腐败”。
政府官员队伍十分庞大,其关系盘根错节,概括一下,无非是一种关系: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一般而言,上级在下级面前是以“官”的角色出现的,而同样是政府官员但级别较小的官员在上级面前,其“官员”意识是萎缩的。特别是一些基层官员,在比自己职位高的官员面前更是自惭形秽,“百姓”的角色意识油然而生。在上级面前,究竟多高级别的政府工作人员算作官员,这在下级工作人员意识中是一个模糊的界定。正因为角色界限的模糊,极易发生角色错位。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当上级布置反腐事宜时,一些基层领导干部或政府里的普通工作人员会觉得自己不是“官员”,反腐与己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其潜意识中,腐败仅是“官员”所为。当自己进行腐败行为后,不以自己是政府官员的腐败为然,反而当作普通公众的劣行。在这里,本来是政府官员的腐败在其意识中被淡化为公众腐败。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实施腐败行为过程中,正在从事腐败活动的官员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意识中悄悄将自己置换为非政府官员。我们知道,政府官员是在政府中工作并具有一定职位的人,而职位就是根据工作目标的需要,具有一定权力和相应责任的工作岗位。权力与责任是统一的、不可分的,失去任何一方,都会与官员职位不符。实施腐败行为过程中的官员已丧失了为国家、人民利益负责任的使命感,其活动并非是国家官员的义务与天职的公职活动,已蜕化成为个人私利(有时是本家庭、本家族、本单位)的疯狂聚敛者,完全丧失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基本品格,在自己意识中(客观而言,是在行动中)不把自己当作具有一定责任与义务的国家官员,而是公众中的普通一分子。在这特定的时刻,针对政府官员制定的反腐预防措施已完全失效。因为在这里出现了严重的角色缺位:反腐措施是针对政府官员的,而政府官员在进行腐败行为时,已在意识与行动中不把自己当作官员。因此,将反腐斗争仅限于狭隘的的政府官员范围,固然能抓住反腐的重点,便于集中力量惩治腐败,但是,忽视公众腐败,会形成一个漏洞,许多腐败分子正是从这个漏洞中冒出的。而公众腐败理论则没有这个逻辑缺失,腐败分子无可利用的角色缺环,有利于反腐斗争的深入展开。
公众腐败已给我们的社会造成相当严重的损害,它毒化着社会风气,败坏着公众的道德情操;它是官僚腐败的温床,孕育着政府腐败;它践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破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正常发育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它已成为一些地方与单位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公众腐败已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了。
原文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