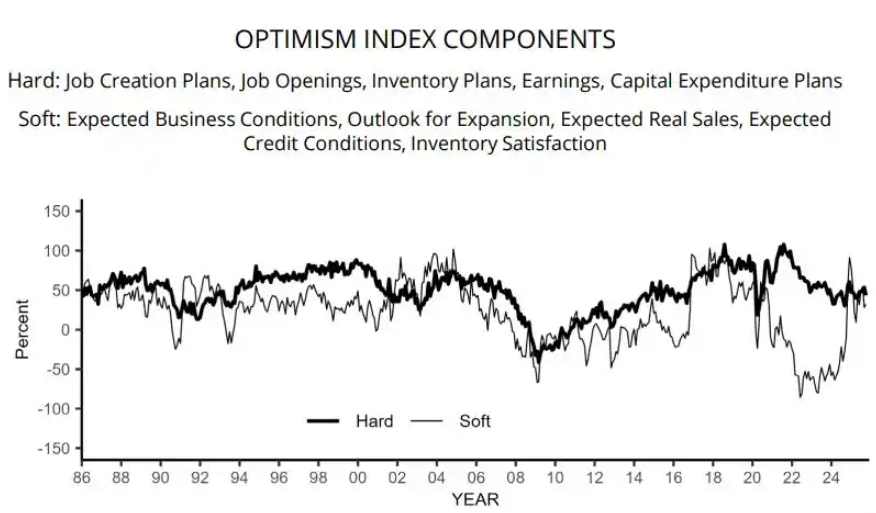从1986年赵玫发表她的第一篇小说开始,30年的岁月从她的笔下悄然流过。前不久,她耗时5年而成的“五叶丛书”结集出版。《矮墙上的艳阳》《八月末》《六宫粉黛》《铜雀春深》《莫奈的池塘》,仅这些书名,就让人看到了细腻、缠绵、哀婉与惆怅,透着一股强烈的吸附力,肆意挑逗着你的某种情绪。
赵玫是一个“让语言生出故事”的作家。她的语言,有着属于她的节奏、语感和腔调。她在不断的变幻中,几乎榨尽了语言所有的内在营养,她将小说里的叙事谋略,也力争完全隐藏在她“绚烂”的语言之中。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的作品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在他们中间一定是有着某种亲和的东西。或者是一种气质的相近,或者是一种精神的相通,或者是某种处境的相似,或者干脆是一种语言方式的接近。”这是赵玫的话,也是喜爱赵玫的读者的真心话。
她的题材,她的故事,她的人物,她的表达,无不透露着一种忧伤而高贵的气质,而那种气质,是出自一个文学女性的精神与灵魂。
作家不能只有一副面孔“关于写作,我总希望它是有变化的。一个作家,如果总是雷同的,雷同别人或雷同自己,就不会有所发展。从开始写作,我就永远在变化。变化,对我而言,哪怕是失败的,都非常重要。整个写作过程中,我永远将自己处于一种颠覆的状态,我觉得创造性对写作乃至整个人生来说都是最最重要的。”
新金融:可以说你是国内较早以女性意识写作的作家,这种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
赵玫: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性别意识。我只是觉得我是个女人,可能对女人更了解,所以我总是更多地去写女人的故事。
变化大概发生在20年前,我应邀赴美参加一个为期40天的国际访问者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我所进行的两个专题,一个是文学,一个就是关于女性的问题。那段时间里,我见了很多美国的女权主义者,其中也有一些作家,她们特别关心女性的生活生存状态。而在当时的中国,关于女性的东西基本是被束之高阁的。回来以后,恰逢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怀柔召开,我也作为天津市妇联NGO论坛的代表参加了那个盛会。这样的背景下,再加上我平时看了很多杜拉斯、伍尔芙、波伏娃女权方面的书,从此我便渐渐对女性写作有了明确的意识,甚至觉得这是我作为女性作家的一种责任。
紧接着我又应张艺谋的邀请,与苏童、北村等几位作家创作小说《武则天》。当时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变化,所以就按约完成了《武则天》,后来又有了《上官婉儿》和《高阳公主》,形成了“唐宫女性三部曲”,就自然而然地被人贴上了某种女权或者女性主义的标签。如果说我有女权主义,那我也是很温和的女权主义者。虽然文字当中会有女权的观念,但我的小说并不是特别尖锐,我并没有刻意地去写女权主义。
关注女性的内心和灵魂,是因为在与男人纠葛的关系中,我对女性的存在有一种很深刻的悲伤,而且在生活当中,女性是比男性更苦痛的。
新金融:回顾你的文学创作道路,哪些时期的经历显得格外重要?
赵玫: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从我写第一部小说《河东寨》时,我就被认为是“先锋派”作家,我不会写那种传统的、古老的小说,那段时期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喜爱外国文学,也感恩中国有一批杰出的翻译家把优秀的外国作品带到国内。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文学是离不开外国文学的,外国文学就好像是给中国文学打开了一扇窗,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输送了极大的营养,有种说法是:“在每一个新时期重要作家的背后都有一个外国作家的影子。”有人喜欢昆德拉,有人钟爱马尔克斯,我喜欢福克纳、杜拉斯、伍尔芙。
但“先锋派”小说写多了,也会感到瓶颈,恰好就遇上了写作《武则天》的契机,让我有了不一样的施展空间。从1994年开始,我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100万字的“唐宫女性三部曲”,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新金融:16岁开始,有8年的时间你在工厂工作,那段时间对你的小说创作有什么重要意义吗?
赵玫:前两年是在钢厂氧气站,后面6年进了宣传科。说起来非常奇怪,那段时间对我小说创作基本没带来什么感觉,好像与我的创作隔绝了一样,我可能只有一篇小说是跟那段时期有关的。
“文革”期间,父母受难,十一二岁的我被送回河北农村老家和爷爷奶奶生活,我的奶奶是基督徒,她常常对我
新金融记者 李香玉
作者:李香玉
让语言生出故事花
-
网站声明:网站内容均为由网友提供,版权归本人所有。任何媒体、互联网站和商业机构不得利用本网站发布的内容进行商业性的原版原式地转载,也不得歪曲和篡改。如需转载,必须与相应提供单位直接联系获得合法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