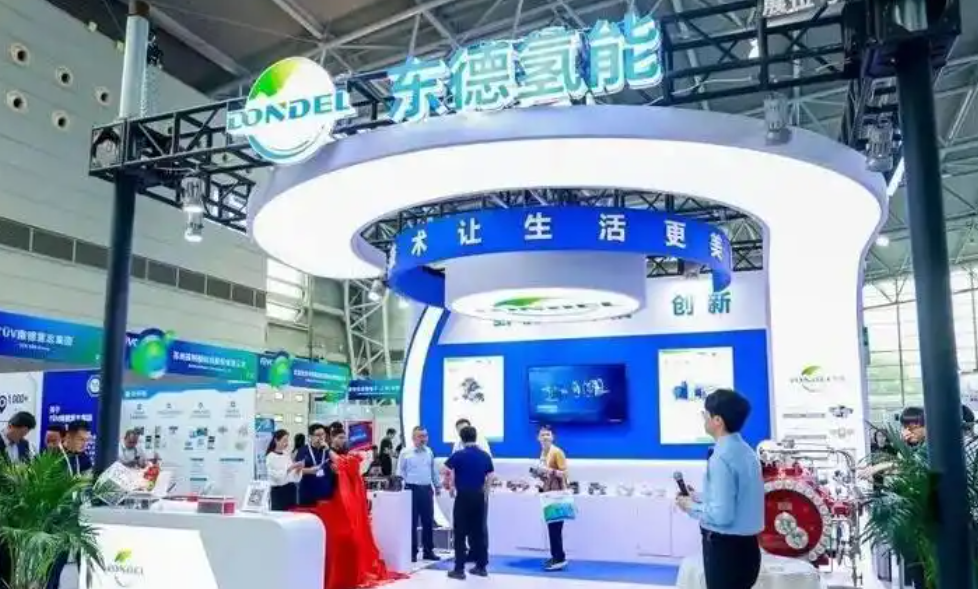幸好有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记录者,她在新闻与文学的交叉路口,捡起被新闻大部队丢弃的宝贝,为人类历史补上不该忘记的一页。

今年诺奖“起锅”爆了两大冷门:一个中国“三无”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奖医学奖。这个话题爆热一阵子之后,已从舆论的“今日头条”旋即被尾随而至的新闻热点赶超,沦为“明日黄花”。二是白俄罗斯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折桂诺奖文学奖。记者出身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跨界拿了文学诺奖,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尤其是出乎中国文学读者的意料。在中国读者印象中,阿列克谢耶维奇默默无闻,其名声远远不及村上春树,这次幸运之星降落在阿列克谢耶维奇,让陪跑多年的“跑男”村上春树情何以堪?更让村上春树的粉丝们失望至极。人们困惑不解的是,诺奖委员会莫非“乌龙”了,竟把高大上的诺贝尔文学奖降格成普利策奖,越界去新闻界“扶贫”了?其实,回望诺贝尔文学奖历史,有记者经历的获奖者有两位数了吧。其中不乏有以纪实成就敲开诺奖大门的幸运之星,只不过,这种类型的获奖者已暌违多年,这次意外回归,让健忘的人们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诺奖的文学项目是不是太不文学、太不专业了?但是,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给彷徨于歧路的新闻业点亮了新的希望:原来新闻还可以这样写?!原来在我们日益狭仄的新闻视野之外,还有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呢!
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乌克兰,长于白俄罗斯,新闻专业毕业的她选择用新闻的方式打量这个沉重、喧嚣的世界。新闻给了阿列克谢耶维奇一双黑色的眼睛,她用这双黑眼睛去打捞光明。与那些喜欢追逐世俗热点、扎堆于浮世喧嚣的媒体同行不同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选择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高冷路径,她关注那些被大时代遗忘、被功利主义的同行们以及被新闻时效忽视的冷话题、边缘人物,以“文献文学”的方式,结合实地采访的文献价值和运用小说技巧的故事性的表达,记录那些被时代“主旋律”遗忘的人和事,用新闻的长镜头记录一个斑驳纷扰的世界,绘就了一个正史之外的历史图景,让我们看到历史背面的沉重记忆。
透过《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战争中没有女性》、《最后的见证人》、《锌皮娃娃兵》、《二手货的时间》等作品,阿列克谢耶维奇让人们看到了俄国革命、二战集中营、苏联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以及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事件的另类叙述。阿列克谢耶维奇这种另类表达,不是故作另类的行为艺术,而是出于她对新闻和文学的整合理解:基于人类命运关怀的真实记录。正因为阿列克谢耶维奇站在人类关怀的高度以及对“人”之命运的深广关注,她超越了对新闻表象的浮泛理解,超越新闻时效和世俗偏好的狭窄视野。“我写的是人类的感受,以及在事件中他们如何思考、如何理解、如何记忆。他们相信什么,又怀疑什么?他们经历着怎样的错觉、希望亦或恐惧?”“如果你回望包括苏联和后苏联时代的整个历史,你会看到什么?一个巨大的坟墓和血浴,一场行刑者与被害人之间永恒的对话,一个被下了诅咒的‘俄罗斯问题’:什么是必须要做的,而谁又是罪魁祸首?革命、集中营、二战、1979年阿富汗战争、巨大帝国的崩塌、乌托邦……而现在呢,又是一个对地球上所有生物发起的挑战———切尔诺贝利。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这就是我书写的主题,这就是我的道路,我的炼狱轮回。”带着对新闻的好奇和历史的追问,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他人止步的地方启程,发掘了他人专业盲区之外的新闻沃土,在这个过程中,围绕真相的追寻,新闻与文学的楚河汉界消融了,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弥合了,实现了阿列克谢耶维奇意义上的完美和谐。
新闻常识告诉我们,新闻是一种选择性记录。这种选择性记录,可谓是新闻业的“铁律”,新闻媒体再有能耐,也不可能做到有闻必录,用新闻复制出一个无限广阔的现实世界来,受到时间和空间以及媒介手段所限,新闻会经常以短视的目光、狭隘的视野去绘制所谓的世界真相。比如,以世俗重要性、戏剧性、反常性、时效性、趣味性、接近性等指标去度量新近发生的新闻。这种选择性记录会造成集体性的失声和失忆,致使许多本该被我们记录或死磕的话题遭遇集体性的冷落。幸好有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记录者,她在新闻与文学的交叉路口,捡起被新闻大部队丢弃的宝贝,为人类历史补上不该忘记的一页。
这不禁让我突然想起列宁的名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